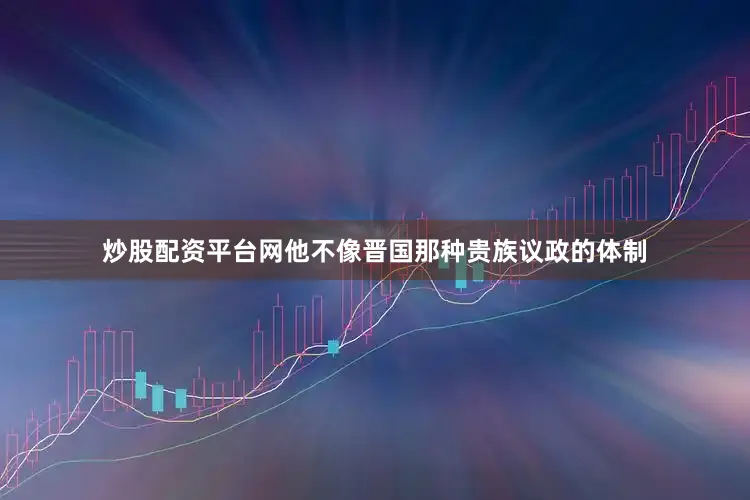
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楚庄王刚登基那几年,几乎没人把他当回事。
三年不理朝政、不发政令,他在干嘛?没人知道,但三年后突然暴起,先杀权臣,再灭列国,还问鼎周天子, 这背后藏着的东西,并不只是“励志”。
登基不到一年,身边就起杀机
公元前613年,楚穆王去世。王位传给了还不到二十岁的熊旅,即楚庄王。
展开剩余91%表面是王位传承,实际上是刀光剑影的起点。
那年楚国局势乱得很, 王宫刚换人,朝堂就乱套,兵权被割裂,贵族各自为营,其中最有权势的两个家族,是“鬬氏”与“成氏”。
鬬克,楚国上柱国,老资格贵族,手上握着禁军实权。
他早就不服穆王晚年独裁,现在穆王一死,年轻的新王又没有靠山,鬬克决定动手。
他勾结公子燮,一位楚穆王的庶子,血脉上虽有资格,却没登基的命运。鬬克怂恿他说,咱们两人联手,不如把熊旅换掉,你来做王。
这不是空谈。鬬克手上有兵,公子燮有人心。
他们趁着王宫变动之际,悄悄调动军队,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 夜里潜入王宫,打算直接劫走楚庄王。
行动很快完成,熊旅被他们劫持,准备连夜送往外地控制起来。
当时还有另一位大臣成嘉在场,鬬克没打算留活口,准备连他一起干掉。可惜行刺失手,成嘉重伤未死。
这时另一个老资格大臣庐戢梨反应过来,他联合叔麋,调动亲兵,追击鬬克队伍。
不久,鬬克、公子燮就被围堵在郢都城外。
城门紧闭,楚军四面合围。鬬克和公子燮逃无可逃。 庐戢梨没有多说一句废话,直接命令格杀,无一生还。
尸体挂在郢都城头三天,警告所有想动心思的人。
楚庄王就这样被“救回来”,一个刚登基几个月的年轻人,差点被干掉。
可真正恐怖的不是刺杀,而是这场政变背后的信号:朝廷内根本没人信他。
熊旅当时虽然“回宫复位”,可权力根本没稳住。大臣、军队、贵族心里都在盘算:这个少年能撑多久?杀鬬克容易,撑权位才难。
很多人忽视了这段史实。史书写得轻描淡写,只说鬬克“欲谋废立”,被杀。可我看到的,是 一次清晰的权谋博弈试探。
熊旅没有立刻清算剩下的鬬氏残部,也没有急着封赏忠臣,而是沉默了。这一沉默,就是整整三年。
三年不发政令,三年不上朝堂,三年不理朝臣进言。
宫里终日歌舞、宴饮,郢都的城门几乎形同虚设。
百姓看得不懂,大臣看得不懂,邻国看得也不懂。一个刚从政变中逃出生天的年轻人,怎么还能天天饮酒作乐?
他是真的废物,还是在演戏?
三年沉寂,他在等什么?
楚庄王沉默三年,这三年朝堂乱,百姓怨,列国纷纷试探。连最亲近的大臣都开始动摇。
有人说他是酒囊饭袋,也有人说他是韬光养晦。可真相只有他知道—— 他还没摸清楚哪些人能信,哪些人要杀。
这个年轻人不是沉迷酒色,而是看清一个局:朝堂上,依旧是鬬克、公子燮那一派的人在撑。他要动,就得一击毙命,不能留后患。
直到第三年,才有一个人冒死进谏。这人叫伍举,朝中清流。他不敢直接劝王,只说了句——“臣闻有鸟,三年不飞不鸣,一飞冲天,一鸣惊人。”
话说完,殿上没人吭声,所有人都看楚庄王脸色。熊旅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第二个站出来的是苏从。他不绕弯子,直言朝政已废,百姓苦难,请楚王重振纲纪。还补了一句:若不听,可杀臣明志。
楚庄王没动怒,也没杀人。他只是点了点头。第二天开始,郢都开始变了。
他亲自召见六位大臣,包括伍举、苏从、孙叔敖,重新编列职权,清查各地封地、税收、军队分布。他还做了件更狠的事: 清洗鬬氏余党,一夜之间,五名上大夫人头落地。
朝堂一震,郢都再也没有人敢质疑这位少年王了。
他还任命孙叔敖主水利。当年楚地频繁旱涝,农田几近废弃,孙叔敖调兵万人修堤建渠,不到两年,收成倍增。
朝堂大变,百姓得益,军队开始重整。邻国才反应过来: 楚国这个“废物王”,突然变了个人。
我认为,这三年沉默,绝不是懦弱,而是布局。他不像晋国那种贵族议政的体制,而是要建真正的君主集权。为了这个局,他忍辱三年, 一鸣那天,直接血洗旧贵族,把地盘、人心、兵权一起抓到手里。
你想想,哪一个二十出头的国君,敢在三年内放空朝政,然后一次出手,斩断半数朝臣?
所以“楚庄王一鸣惊人”不是神话,而是一次实打实的权谋大翻盘。他忍得住,藏得深,下得狠,收得稳。这才是真正的“霸主开局”。
史书里用一句“政令大举”带过,可背后那些血和火,才是真正令人发冷的东西。
楚国的变化也从此真正开始了。
邲之战爆发前,楚国先动手
楚庄王改革之后,没有停。接下来几年,他开始做一件事—— 征战列国,向中原开路。
最先倒霉的是庸国。这个小国曾是楚国的属地,后来趁楚国混乱独立。
楚庄王重整旗鼓后,调集两万兵马,亲征庸地,短短数月灭国。
庸国君主自缢于祭坛前,尸体都没收回来。
灭庸之后,熊旅没有停。他转头对准了申、息、蓼、陈、蔡、郑这些楚国北方的小国。
这些地方夹在楚、晋之间,一直摇摆不定。楚庄王决定一举清扫,彻底为北伐铺路。
尤其郑国,形势最微妙,郑夹在晋、楚两大国之间,两头讨好,却又屡次背楚向晋。楚庄王忍无可忍,亲征郑地。
郑国国君跪地求和,割地赔礼才算了结。郑国从此改旗易帜,归入楚国势力圈。
到了公元前598年,楚国已经横扫七国,控制了整个汉水以南。接着最关键的一场战争爆发了—— 邲之战。
晋国当时是春秋最强,三家大夫把持政权。楚国崛起对晋是巨大威胁。
两国在郑国边境对峙,楚庄王调兵十万,晋国出兵八万。两军对阵,郑国成了导火索。
战前,晋军迟疑不决,贵族意见不一。
有的主张速战,有的主张撤兵。楚庄王抓住这个机会,派密探潜入郑国城内,策反郑国守将,城门在夜里被打开,楚军一夜之间突入郑都。
晋军闻讯大乱,前军未稳,后军混乱,楚庄王下令猛攻,一口气追击至黄河边境。
这是楚国第一次真正把中原霸主打得溃不成军。
整个郑国尸横遍野,野地里堆起数千具晋兵尸首。
史书记载,楚军原想立“京观”——将敌人尸骨堆成小山,立旗示威。楚庄王却下令停手。
他要的是威信,不是血腥。他命人掩埋敌尸,并在城头祭天,以礼示众。
这一刻,谁都明白,春秋的霸主换人了。
我觉得,楚庄王之所以能成功,不只是兵多将广,更关键是心狠。
晋国贵族议而不决,楚国一言九鼎。 楚庄王从不是“讨伐者”,他是猎人,盯准猎物后绝不放手。
而那场邲之战,也是他一鸣惊人后的第二波高潮—— 不靠联盟,不靠口号,靠的全是铁与血。
王帐之中,忠与死、礼与杀交织
楚庄王权倾朝野后,有个细节常被忽略—— 他在宫廷的每一次“赏赐”,都藏着对权力的警告。
有一年,宫中宴请群臣。庄王召许姬侍酒。许姬是宠妃,身姿婀娜。正举杯时, 有人牵她衣袖,缨带落地。
宫宴之中,这种事就是羞辱王威。
楚庄王没有当场发火。他反问群臣:“你们看到谁帽缨掉了?”
所有人都低头不语。这时,有臣子主动解下自己帽缨,说:“可能是我。”其他人纷纷效仿。 不到一刻钟,满殿皆无缨带。
楚庄王轻轻一笑,没有惩处任何人。可是我看到的,是另一个意思: “我能赏你们荣,也能剥你们冠。”
又有一年,他爱马病死,下令要用“上大夫之礼”来葬马。满朝震惊。谁敢违旨?这时,优孟进谏,说:“葬马若以大夫礼,将来你死了,臣等该以何礼送你?”
楚庄王听后,沉默很久,最后改了主意。马以“庶人”葬。
这不是愚忠得势,而是清醒的帝王术。楚庄王能听忠言,更懂借机立威。
优孟不是一个说话好听的角色,可正因他不奉承,才让楚庄王更信服。
最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在邲之战后。
那场战役中,有位勇将名叫鬻熊。曾在宫宴帽缨事件中,被楚庄王当众点名,差点获罪。可楚庄王留了他一命。
邲之战中,鬻熊死战到底,身中十数枪,尸体被敌军挂在郑城西门。
楚庄王亲临收尸,赐以将军之礼安葬。
宫中一次宽恕,换来战场上以命相报。这就是楚庄王的统御逻辑:我给你体面,你要为我死。
他的王权,不靠恩,不靠义,靠算计和收放之间的分寸。
有人说他“仁”。我不同意。楚庄王从头到尾都冷静得让人发寒。
对敌国,他一刀斩尽;对朝臣,他收放自如;对百姓,他施政务实。
但他的核心只有一个: “权”,所有人都要服从。
一鸣惊人不是浪得虚名,是他用整整三年的等待换来的机会,用无数人头换来的威信。
他的霸业没有靠祖宗,也没有靠联盟。他不走寻常路,不讲虚礼。他靠算,靠忍,靠杀。
史书写得文雅,我愿意说实话——这是一位用人头铺出的帝王。
发布于:福建省易云达配资-如何股票配资-配资网站推荐-线上股票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