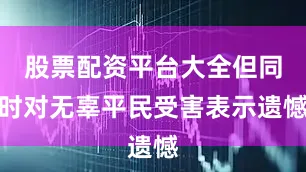9月以来的四十多天,河南被笼罩在连绵的阴雨之中。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全省平均降水量达34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6倍,是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正是玉米、花生等作物丰收的时节,农户们冒着雨,想尽办法徒手抢收,但许多时候还是只能眼睁睁看着好不容易从夏天旱情里保住的庄稼被淹在地里,发霉长芽。
极端天气频频侵袭,农户们过往的经验渐渐失灵,脆弱又无奈。种了70多亩地的南阳农户张秀还不敢计算这次的庄稼的具体损失有多少钱,但可以肯定的是,“赔都赔得不得了”。
抢收
雨还在下。10月17日,河南南阳市社旗县郝寨镇的村民张秀从家里望出去,一片“沟满河平”。从前一天夜里开始,大雨不住地往下泼,田间道道深沟涨起水,漫溢出来,“下得满满的,都分不清哪个是路哪个是沟了”。张秀看得心焦,她惦记着家里还没收割的29亩玉米地,但雨大得她不敢出门。
进入9月以来,河南的这场秋雨已经下了四十多天。本刊采访的多位农户都没有想到,这场雨会下这么久。其实对于起初的几阵雨,农户们是有些高兴的,觉得能缓解持续整个夏季的旱情。但到了9月中旬,玉米成熟该收割了,雨却还在下,眼看着玉米杆子泡在水里,叶片变得枯黄,剥开外皮露出的玉米棒子已经发霉长毛,张秀开始着急,她等不到放晴,冒着雨和老公婆婆掰完了一亩多地的玉米。阴雨天还在持续,张秀家还没来得及收剩下的29亩玉米,紧接着,花生也在9月下旬成熟了。为了不让花生全部沤烂在地里,她们只好先去收更值钱的花生。
展开剩余89%烂在地里的玉米(受访者供图)
土壤过湿,轮式收割机的轮胎会陷进地里,惯常的机械化作业此时不太行得通,很多农户只能自己徒手收割。张秀穿着胶鞋踩进花生地里,半条腿深的泥巴一下子灌进鞋里,感觉一只脚有四五斤重,走不了路,只好脱掉鞋子光脚下地。也没法蹲坐,张秀只能弯着腰一株一株费力把裹着泥块的花生薅出,指甲都被磨断。一天下来,她的腰比肌肉拉伤还疼,晚上睡觉要固定一个姿势,动都不敢动。
收割手成为秋收期间最忙碌的角色之一。河南驻马店市的陈丽和丈夫拥有一台能下湿地的履带式收割机,这一个多月来四处奔波,每天都睡在车上,“不是通宵也是加班”,一天能收割五六十亩地。地太湿,收割起来负荷大,履带等配件损耗翻了三四倍。在河南省内,陈丽夫妻帮收割的基本是玉米,很多都霉烂发芽了,想起她就忍不住叹气,“今年真的不容易啊,玉米收出来跟羊屎蛋子一样。”
2025年10月8日-12日,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秋收遇上阴雨天,面对当前天气不利因素,当地农民打响抢收秋粮“保卫战”,铆足干劲抢收、抢储、抢烘。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摄(视觉中国供图)
在豫北,濮阳郎中乡的凤娥自玉米成熟后就睡不好觉了。每天夜里她都会起来三四次,看看雨停没停。她和丈夫承包了一百多亩地种玉米,是村里最大的种粮户。在常州打工的女儿和上大专的儿子都回来帮忙抢收,凌晨五点起床,只要雨一小就下地,掰玉米、装袋。儿子埋头背着40斤的玉米袋,一脚深一脚浅地淌过一百多米泥地,要花上十分钟,期间得用手抓着身侧的玉米杆,不然就会摔倒。为了方便干活,他们不穿雨衣,凤娥看着儿子湿透的衣服,一阵心酸,“我无论怎样吃苦,感觉都没事儿,也不觉得苦,但是看到自己的孩子那样,我的泪就流下来了。”
辛苦着和天抢时间的农户们大多有着同一个朴素念头:不能让粮食烂在地里。张秀的婆婆今年62岁,种了一辈子地,最近只要在地里看到一颗遗漏的花生,就心疼地赶紧捡起来装进衣服口袋,“说捡一个花生就是一颗金子”。想着地里没收的几十亩庄稼,婆婆又愁又急,有时拔着花生就哭起来。她每早天不亮就起床,把两个胶袋剪开后一针一针缝成大袋子,方便背花生。即使得吃止痛药才能下地,她也要在地里干到天黑,都不舍得回家。
晾在地上的花生(受访者供图)
抢收如此迫在眉睫,也有着经济上的考量。李伟是商丘市睢县蓼堤镇的农户,租了5亩地种玉米,他给本刊详细计算了每亩玉米地的成本:地租一年800元,要买种子、化肥、除虫药、矮壮素,加上浇水的电费、播种和收割的机器费用,一亩地成本1200元左右。正常情况下,每亩玉米能收成1500斤-1700斤,一斤卖1.1元,但如果是被打湿的玉米,售价砍半,这样一亩地要倒亏好几百元。
许多抢收不完的农户,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烂在地里”。凤娥有块承包地在村南边的低洼处,30多亩玉米来不及抢收,只能先留在地里,等雨完全停后,拿小型抽水泵把水慢慢排走。在河南最主要的水稻种植区信阳市,雪莲61岁的父母只在9月初约上一次收割机,收了十几亩水稻,之后就再也约不上。国庆雪莲回家下地,掰开稻谷一看,里面都是深灰或者黑色的霉斑,对于剩下还没能收割的20亩水稻,雪莲说,“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60年一遇的秋雨
李伟今年52岁,这是他记忆里头一次遇到这样连绵的阴雨天,“像江浙那带的梅雨季”,往常早晨洗的衣服中午就能晾干,现在晾上两天“还是潮乎”。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进入9月以来,河南先后出现10轮大范围降水,全省平均降水量达349.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6倍,是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时间上,河南平均阴雨日数达25.3天,较常年多14天。
乔江方是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河南省秋粮生产专家组成员。他告诉本刊,往年正常情况下,秋天天气较为晴好,即使下雨一般就两三天。而过去的四十多天里,他印象里只见到6、7次太阳。连绵阴雨对正处于收获季的农作物无疑会产生不利影响。以玉米举例,乔江方表示,其一是光照不足,玉米中后期的籽粒灌浆会受阻,从而减少产量。二是玉米表面长时间湿润,容易滋生霉菌,毒素含量增加,影响质量。
这场60年一遇的秋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人们过往的应对经验。乔江方8月参加过两次省气象部门组织的预判会,当时预判到9月的降雨量会比往年更大,“但不知道会偏多这么多,还持续这么长时间”。9月中旬开始,乔江方到乡村一线指导如何在连阴雨天气抢收,“基本跑遍整个河南”。各方也都在行动,据河南日报,河南组建了742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跨省引进3080台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向农民群众公布全省4963台烘干机械位置和联系方式,先后安排5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烘干机械奖补、秋粮收获补助和调度农机。
泡在水里的玉米地(受访者供图)
更异常的是,在“秋涝”之前,河南先经历了严重的“夏旱”。河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李芳此前接受采访时指出,1961年以来,河南仅2014年出现过类似“夏旱秋涝”情况,但当年6—8月降水偏少四成、9—10月偏多1.1倍,而今年9—10月降水偏多超2.6倍,异常程度更为突出。
对农户来说,这些被泡在地里的庄稼都是他们从旱情中保住的。浇水这一动作贯穿了凤娥的整个夏天。浇一轮要半个月,今天刚浇完,明天就看到玉米叶卷起来,又旱了,她一共浇了3轮。从6月种下玉米开始,凤娥就守在水井旁,有时十几分钟就要挪一次水管,只有浇300多米长的田地时,能有四小时的连续休息时间。伏天太热,凤娥一天要喝七八瓶水,把毛巾打湿后盖在头上,再戴上宽檐帽子,能凉快点。抗旱还有经济成本,李伟说,一盘60米的“小白龙塑料袋”(长塑料管)要百十来块,一块地要用好几盘,“比较心疼,都不愿意浇,除非没办法了浇一下。”张秀为了浇水都睡在地里,“天天没日没夜的浇水,心里面总想着浇完到时候能有个好收成,一直都是抱这个希望。”
即使把庄稼抢收回来,许多农户没有充足的通风晾晒条件,庄稼还是会发霉长芽。乔江方说,正常玉米收获的水分含量在20%以下,这次秋雨导致玉米水分含量在35%以上,容易积热加速霉变,有效的方法是烘干。乔振群在南阳唐河县经营烘干点,两台烘干机24小时连轴转,一个月来烘干了四五千吨玉米,一吨收费150元。乔振群告诉本刊,城郊乡8万亩地,有十几个烘干厂,他的烘干机使用率翻了一倍的情况下,农户们依然要排队三天才能烘上,找他的以种几百上千亩地的大户最多。
而在很多个体小农户看来,烘干不是最便捷实惠的选择。其实李伟也想去烘干,但政府修建的烘干塔每仓要十几二十吨起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邻居种三四亩地,收五千斤玉米,量太少,每家玉米质量、干湿度也不一样,很难凑起来一起烘干。如果找私人经营的烘干点,李伟觉得费用有些高。家种水稻的雪莲回忆,往年几乎用不上烘干机,只有偶尔晒粮中途遇大雨才应急使用。张秀也没有去烘干,而是腾出自家新建的二层房子来晾,主要顾虑烘干的价格,“那个应该好贵吧。”
秋雨影响的不仅是秋收,还有下一茬农作物的播种。张秀判断,今年的小麦可能种不上了,因为花生还没收割完,地湿也无法旋耕。李伟说,往年他两周前就种下大蒜了,现在还不敢播种,害怕坏根,得等土里的水分渗下去些。他有些忧心产量,“种的时间晚了,温度低,明年大蒜可能要减产。”
受损的农户
32岁的张秀还不敢计算这次的庄稼的具体损失有多少钱,但可以肯定的是,“赔都赔得不得了”。没收上来的玉米和花生都有20多亩,收上的花生里有一大半湿坏,晒干后去卖,收粮商也因为质量问题拒收。
放心不下父母孩子,张秀夫妻每年一半时间在外打工,5-11月回家种地干活。张秀和丈夫郑楠是高中同学,婚后一起去广东中山打工。张秀在纺织厂做内衣肩带,一天站12个小时,在30多台机器间跑动,月工资四五千。郑楠在五金厂做工,一个月五六千元。为了多攒下点钱,夫妻俩能省则省。饭在工厂食堂吃,只花三四百元在城中村租了一间10平米的单间,往返河南和广东坐的是十几小时的大巴车。
枯萎的玉米杆(受访者供图)
对于这个有着四个孩子的家庭,种地是收入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四个孩子分别13岁、12岁、7岁和6岁,都是上学的年纪。父母身体不太好,一直在吃药,止疼的、降血压的都吃,一个月药费千把元。养家一年得十来万,张秀夫妻打工半年挣五六万,剩下靠70多亩地,正常收成一亩地能挣六百元,加起来将将够上收支平衡。张秀说,上有老下有小,家里攒不下钱,也顾不上考虑为孩子存钱这类更长远的事,一切努力先解决眼下的生计问题。
张秀说,种地比打工辛苦,也更不稳定,但孩子们逐渐长大,她需要更多地留在家里。夫妻没回来时,在乡里上初中的大女儿总是闷闷不乐的,吃完饭就把自己关进房间,有什么事都藏在心里,张秀打电话时问起,女儿就只摇头,更不会和爷爷奶奶说。张秀回家后,大女儿明显活泼起来,“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吃了什么饭,学了什么习回来都说。”12岁的儿子变化也很大。过往爷爷奶奶说一两句他就容易发火吵架,“像叛逆期”,父母回来后变得很听话,让他做家务也立马就去。
和张秀类似,48岁的凤娥也离不开家。五六年前,她会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去过广东、杭州和山东的食品厂、玩具厂。直到女儿陆续生下两个孩子,年轻的夫妻俩去常州打工,放在邻村的丈夫家里由婆婆帮忙带,凤娥觉得自己也要帮衬女儿带外孙,于是不再出门。
凤娥家的收入主要靠这一百多亩地,正常一年收入七八万,成本三万。种地赚得不多,家里的经济压力也存在,丈夫是村干部,工资一个月一千多元。20岁的儿子在上大专,一个月生活费2000元。家里前几年盖了一栋两层楼的新房,凤娥在装修上很用心,铺了大理石地砖,楼梯安装了木质扶手,盖房的欠款也得慢慢还。眼下赚的钱过日子是够的,但凤娥想到,将来公公婆婆两位老人如果有小病小痒住院需要钱,更大头的是儿子结婚的开销,“怎么也得四五十万”。所以凤娥不舍得折价一半卖湿粮,好在自家有十几万斤容量的粮仓,凤娥把玉米放进四面通风的铁丝笼里,每半天去翻动检查,如果有发霉的就铺开重新晾晒,希望最后还是晾成干玉米棒再卖。
烂在地里的玉米(受访者供图)
52岁的李伟是村里少有的留在家里干庄稼活的“70后”,更多村民选择外出打工。他年轻时当兵,退伍后也在工地上做过工,前些年,两个孩子在县里读中学,需要接送,加上2016年村里在脱贫攻坚政策下建了大棚,他就靠大棚挣钱,春种甜瓜和西瓜,夏种蔬菜,再种几亩玉米。李伟说,现在年龄渐长,也没有什么技能,外出打工已经很难谋生,“就靠这点地了”。
“我两口子现在所有干的都是为了孩子。”李伟的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女儿正在睢县县城实习,儿子在郑州读大二,每人每月1500元生活费。李伟夫妻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他的衣服7元一件,菜就吃大棚里自己种的,挑便宜的土豆、绿豆芽、白菜,辣椒卖得贵,就不吃。把两个孩子供上大学后,李伟没攒下什么积蓄,现在只希望孩子毕业后能找着工作,能养活自己,“别再回来种庄稼都行”。
10月18日,凤娥发来一条视频,她抢收到粮仓精心照料的玉米还是有许多发了芽,远远望过去像一丛嫩绿的青草。她没有抱怨什么,转而分享起了把玉米收进粮仓时的一件事:上周的一个晚上,凤娥洗完碗出来,看到粮仓院子里三四个邻居主动搬来凳子,默默坐在玉米堆前帮她剥皮。对门大哥有严重腰间盘突出,但也想搭把手,就举着太阳能灯帮忙照明。邻居们也没说啥,只是冲她笑。所以凤娥想着,天灾不由人,不管收成怎么样,她能做到的是好好把玉米种下去、收上来,“把当下能做的做好就行了”。
凤娥粮仓里发芽的玉米(受访者供图)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发布于:北京市易云达配资-如何股票配资-配资网站推荐-线上股票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我要配资网我们直接拿出最大的诚意
- 下一篇:没有了